全职妈妈回归职场的苦恼啊,真是越来越难了
- 类别:职场八卦 时间:2023-11-04 浏览: 次
- 我这全职妈妈回归职场的苦恼啊,真是越来越难了。更别说回到原来的岗位了,这是全职妈妈们重返职场时首先面临的问题。要回归职场后,我们还会面临经济和观念的双重束缚。我们的意愿和现实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,说明全职妈妈正陷入困境。
继续用古风幽默的语言写第一段:
作为一名全职妈妈,我很担心重返工作岗位。 越来越难了。 近年来,找工作并不容易,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来说。 生完孩子后想要重返工作岗位是极其困难的。
我的家人使用大数据来研究这个问题。 我们将1964年以后出生的职业女性与建国初期、市场转型初期就业的两代女性进行比较,观察她们从第一个孩子出生到成年的18年。 就业状况。 研究发现,产后未能重返工作岗位的母亲比例正在增加。
在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,我研究的第一件事是女性生育后收入的变化。 研究发现,当女性成为母亲后,如果她们不退出劳动力市场女性在职场的弱势地位,她们的收入就会下降。 后来我们发现中国的全职妈妈越来越多,所以我们做了这个研究。
唉,年轻一代的全职妈妈中没有重返工作岗位的比例仍在增加。 以前单位制度下,休完产假就可以回来工作。 简单又方便。 但国企改革后,年轻一代不工作的全职妈妈比例迅速上升。
教育对女性就业的保护作用也有所减弱,这可能是整个社会文凭贬值和女性教育快速扩张的结果。 现在高学历的人越来越多,刚毕业的大学生找工作就难了。 雇主自然不会选择还需要照顾孩子的母亲。
生完孩子后,妈妈们在体力和精力上就已经处于劣势。 生完孩子后,我们可能无法举起重物,还可能会出现腹直肌松弛的情况,无法完成很多需要体力的工作。 而且,下班后还要花很多时间照顾孩子。 如果晚上睡得不好,白天就很难集中精力处理那些消耗能量的任务。
更不用说回到原来的岗位了,这是全职妈妈重返职场面临的第一个问题。 技能贬值是最直接的原因。 比如程序员掌握的技术会落后,策划技能会从图片升级到视频,职业生涯会中断几年,全职妈妈要重新学习一些技能。 因此,宅在家里、远离社会的时间越长,重返职场就越困难。
你什么时候回来? 这个问题一般与孩子的年龄有关。 一个集中的时间点是孩子3岁的时候。 进入幼儿园后,他不再需要这样的重症监护,大约有一半的妈妈会重返工作岗位。 另一个时间点是孩子6岁进入小学,有的妈妈在家照顾孩子的时间较长,等到孩子上大学了才考虑重返工作岗位。 但如果中断时间较长,就很难再找到工作了。 时间越长,就越难回来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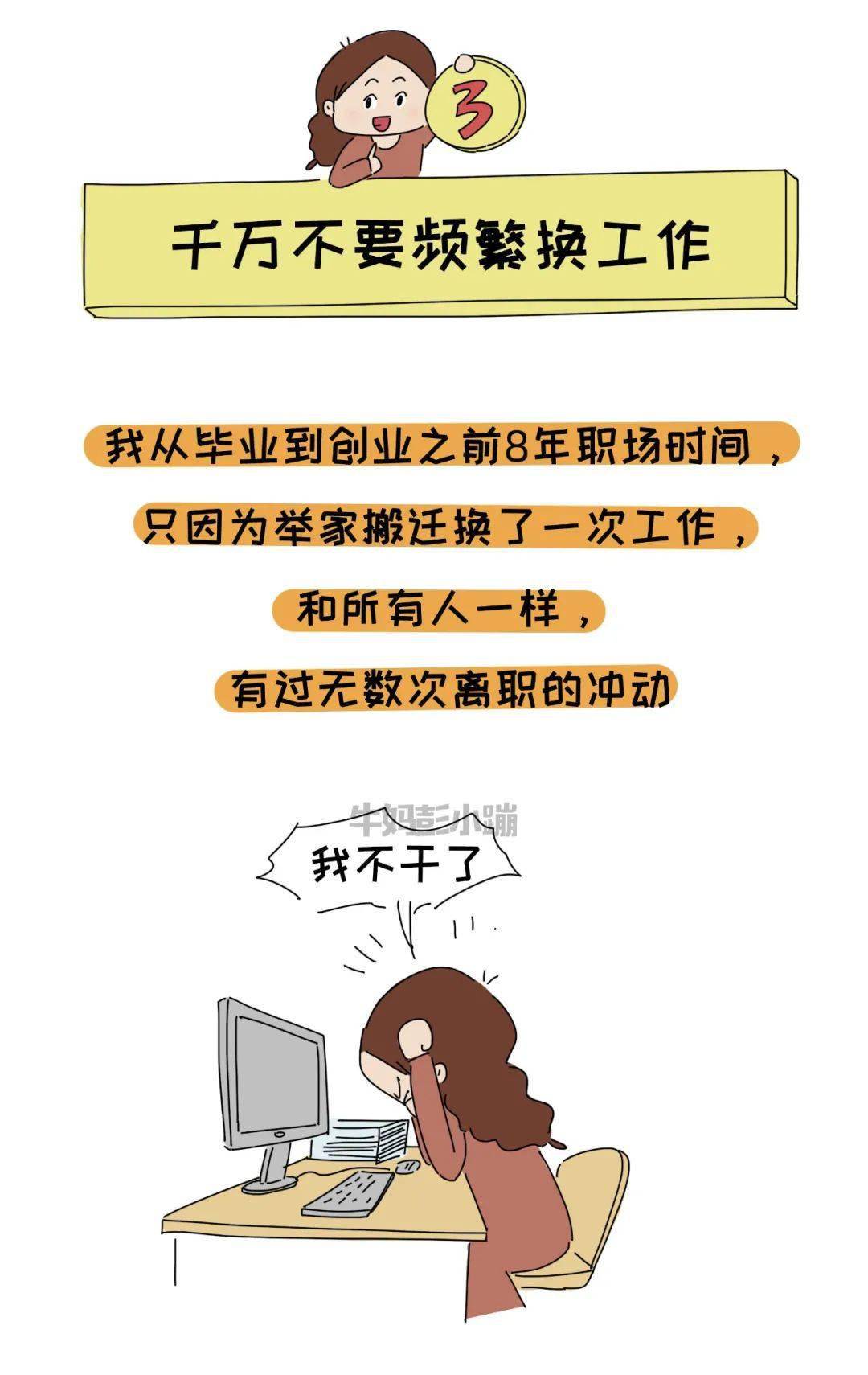
唉,对于不同代际的妈妈来说,重返职场的时间更长,难度也更大。 东亚地区的年龄歧视观念就在这里。 当全职妈妈回来时,她们可能已经30多岁了。 即使她们没有生过孩子,到了35岁还是要考虑工作。 作为一个竞争力不强的群体,全职妈妈自然更难。
必须考虑到母亲身份意味着就业机会有限。 996工作时间对我们来说不太可能。 我们更适合工作时间短且稳定的工作。 但我们往往达不到这个门槛,所以很多人只能选择非正规就业。
我们还研究了调查数据发现,年轻一代女性在第一次生育后,会越来越多地选择非正规就业或个体经营等灵活的就业方式,而且这种选择的比例明显增加。 而且,女性产后重返工作岗位越晚,选择灵活方式的女性比例越高。
唉,即使我们全职回到职场,很多妈妈仍然从事着一些行政文书工作。 没有特别大的晋升空间,也不会承担很多繁重的工作。 这被称为“母性惩罚”。 也就是说,当女性成为母亲后,她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待遇将会遇到困难。 用人单位打着“为你好”的幌子“照顾”我们,但这实际上阻碍了我们在职场的发展。
职业性别隔离也存在。 在生孩子之前女性在职场的弱势地位,我们可能会从事需要精力和技能的职业,比如金融、医生、律师等,工资和声望都比较高。 但成为母亲后,我们进入了更多收入和威望较低的“女性职业”,比如护士、幼儿园老师。
即使我们很多妈妈没有受家庭照顾影响的工作,但职场也会认为我们有很多照顾责任,不会给我们安排需要经常出差、需要大量精力和时间的管理类工作。 成为父亲后,男人将获得“父亲红利”,更容易找到工作、升职、赚取更高的收入。 因为老板觉得他们比较稳定,会更加努力的工作养家糊口,不会随便辞职。
这都是社会观念带来的歧视:即使我们有能力,也因为是母亲而被认为“不好”。
这种“被动主动”实在令人郁闷。 社会总是要求妈妈们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照顾孩子。 如果你把孩子交给保姆,就会被说成是一个不合格的母亲。 如果你刚生完孩子,没有用心照顾,或者提前停止母乳喂养,你的家人和社会就会批评你,问你为什么生完孩子就去上班? 这种要求在社会学中被称为“强化母性”。
在妇女解放运动初期,妇女不工作被认为是一件坏事。 那时没有全职妈妈,大家都要去工作,形成了鼓励女性就业的文化。 然而这种文化逐渐衰落,“密集母性”的要求让女性被视为孩子的主要照顾者。
在一些小学面试时,他们会问你父母是做什么的。 他们希望有一位家长能够全职照顾孩子,陪伴孩子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。 通常是母亲。 许多家庭甚至互相竞争。 比如你可以送孩子去暑期游学,但我可以直接带着孩子去。 这样,我可能是一个更称职的母亲,形成父母之间的内卷。
以往的研究表明,无论是国内家庭还是国外家庭,全职妈妈的地位都相对较弱。 没有独立的收入,在家庭中就没有发言权。 我们可以工作,但我们没有决策权。 对主观感受和幸福感的研究还发现,一个曾经优秀的女性如果被困在家庭中,她原来的自我认知与实际情况不符,可能会影响她的心理健康。 许多社会联系也会消失——朋友消失了,同事消失了,社交网络消失了。 这种效果是无形的,直到我们需要利用社会资源来做事并向别人求助时才会出现。
此前有机构调查发现,90%的全职妈妈希望重返工作岗位,但从数据中我们也可以看到,中国全职妈妈的比例在持续增加。
原因之一是经济考虑。 很多时候,请保姆的成本是非常高的,支出可能和很多妈妈的收入差不多。 但如果你抚养自己的孩子,就没有经济成本。 这意味着在家庭中,母亲的贡献将会贬值。 过去有新闻报道过一位女性,她是一名全职家庭主妇,做了大量的家务。 结果离婚时她只损失了1万元。
还有能量的安排。 现在很多家庭的孩子越来越少,妈妈们也愿意在这个孩子身上投入大量的精力,对孩子的要求也越来越高。 以前单位制下,上班就可以直接送孩子去单位幼儿园。 市场化改革后,国家对儿童保育的负担也有所减轻。
经济收入低、工作条件差、受教育程度低的女性在成为母亲后往往容易退出劳动力市场。 一方面,我们要考虑经济和就业问题,看看如何才能对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更加有利。 毕竟很多家庭只能看到眼前的经济损失。 另一方面,她们还要承受来自丈夫、公婆、父母的压力。 我们之前做过居住安排对生育过的女性的影响研究,发现与“同居”(与男方父母同住)相比,“同居”(与女方父母同住)对女性生育后的就业几乎没有影响。 没有影响。
而且,这些女性往往不明白,失业后她们将失去医疗保险、养老保险等福利保障。 有学者发现,许多从事非脑力工作的女性在怀孕后会主动辞去工作,觉得自己不适合这份工作。 但她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可以享受产假福利和产假。 这是法制教育的缺失。
总的来说,女性往往将全职母亲视为她们自己的主动选择。 他们表示,育儿保姆的市场价格很高,所以他们愿意为了家庭做出牺牲。 但所谓“主动”实际上是“被动主动”。 看似自由的个人选择其实并不真正自由。 它们的背后是社会结构的推动。 社会资源较少的女性处于弱势地位,在经济和思想的双重压迫下没有太多选择。
回到职场后,我们依然会面临经济和思想的双重束缚。 比如我们的孩子要上补习班,家庭开支很高。 我们被迫接受低价值工作或兼职工作,以便为家庭提供一些经济支持; 而社会观念要求我们承担很多育儿责任,承担起所谓的“母亲的职责”。 一边工作,一边照顾孩子,妈妈的日子真不容易。
愿望与现实的巨大差距,说明了全职妈妈的困境。因此,个人能做的其实很有限,雇主能做的也很有限。 我们应该从国家层面出发,基于舆论、理念、财政投入等提出措施,切实解决这一问题。
“时代造就英雄。” 在这个日新月异的社会中,女性重返职场之路并不平坦。 唐代文学家白居易曾说过:“自古无死者,其忠义必被历史所铭记”。 只有保持坚定的信念,才能战胜逆境,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。 读者朋友们,对于这个问题,您怎么看呢? 请留下您的宝贵意见,让我们一起讨论。
